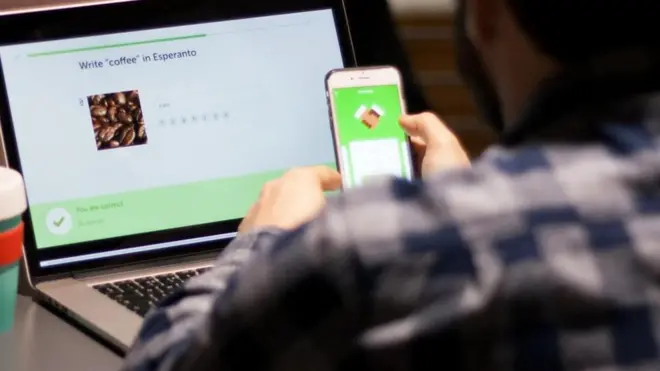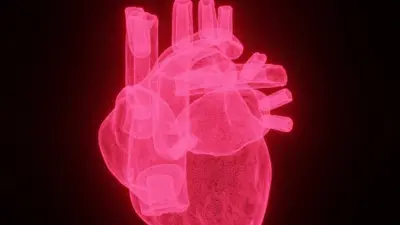為何印尼人很少說官方語言印尼語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 Author, 大衛·費特林
- Role, (David Fettling)
在印度尼西亞日惹市(Yogyakarta)一個安靜街區的路邊小攤上,一名婦女切碎西紅柿、豆子和菠菜,還有一個紅辣椒,再拌上花生醬,然後將做好的印尼什錦沙拉(lotek)遞給那些騎著摩托車排隊或坐在藍色塑料凳子等候的顧客。她對我充滿著疑問,好奇我是誰,而我對她也有著同樣的感覺。為了與她這樣的當地人聊天,我搬到了印度尼西亞居住,還參加了印尼語的強化學習班。但即使我已上了數百小時的印尼語課程,今天我仍然聽不懂她在說什麼。
她說的每句話我聽起來像是只有半個音節。我確實能聽出一些熟悉的單詞,但是少得可憐。我想知道她在這個城市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她對這個年輕的民主國家以及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國家,其政治和文化的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有什麼樣的想法。但我並沒有得到答案。
她把我買的食物用報紙包好遞給我,我能讀懂報紙上的文——'標凖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 baku)',我心想,這就是教科書用的印尼語。我的老師在課堂上將這種語言稱為"Baku"(印尼語中意為"標凖形式"),強調這是我們正在學習的印尼語的標凖版本,這是國家的官方語言。老師強調補充的這句話在那時並沒有引起我的重視,但現在我才知道那是多麼的重要。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現在東南亞地區,組成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現代國家的數千個島嶼至今仍有數百種語言流通,而印尼語的前身馬來語在一千年來因為東南亞海洋貿易的需要,成為這個地區貿易和交流之用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而得到了發展和傳播。馬來語被認為語法簡單,無社會等級意識,比其他地區語言更容易學習。雖然幾乎不是任何族群的母語,但隨著印尼馬來地區各民族的交往溝通,馬來語逐漸成為他們彼此溝通的通用語言。
然後,在20世紀初期,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在策劃脫離荷蘭殖民統治而獨立時,一致同意將擁有著較大詞匯量的一種馬來語改良版本,命名為印度尼西亞語,以作為即將獨立國家的官方語言。根據康奈爾大學的印度尼西亞學者本尼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馬來語"簡單而靈活,可以迅速發展成一種現代的政治語言"。
選擇印尼語目的是為打破民族溝通障礙,促進300多個民族融入新的國家,印尼獨立在1949年正式得到承認。當時的想法是,不把任何主要的民族,包括爪哇人(爪哇語作為一種高度複雜的語言有大約40%的人口在使用)所使用的母語作為官方語言,這樣才不會產生或強化各民族間的不平等,新生的印尼語將有助於印尼這個多民族國家維持統一。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但實際上,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今天,標凖的印尼語並沒有與馬來語有太多不同之處,人們很少在日常交談中使用。聽到我說起在路邊攤與當地人聊天時遇到困難,我的語言老師安迪妮(Andini)告訴我,人們認為印尼語太過'kaku',即印尼語死板和僵硬之意。此外,人們有時會發現印尼語不足以表達他們想要的東西。安迪妮承認,她經常有著這種挫折感,有些時候印尼語無法將意思表達清楚,她就想要使用她家鄉的東爪哇方言中的詞匯和表達方式。
產生這個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印尼語本身:印尼語比大多數語言的詞匯量少。《雅加達郵報》的安迪·巴俞尼(Endy Bayuni)寫道,印尼小說翻譯成外文後往往好過原著,而外國小說翻譯成印尼文讀起來會嫌"累贅和重覆"。但也有一個政治層面的原因。根據波士頓大學人類學副教授南希·傑史密斯-荷服勒(Nancy J Smith-Hefner)博士的說法,因為印度尼西亞人是在學校學習印尼語,然後成年後也主要是在政治演講中聽到這種官方語言,他們便將印尼語與社會的單一化視為一體。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1998年的蘇哈托(Suharto)獨裁統治期間,因大力提倡印尼語,扼殺了許多個人和文化表達形式,印尼語的單一化現象更加嚴重。奧克蘭理工大學文化、話語和傳播研究所的奈尼·馬丁-安娜提阿斯(Nelly Martin-Anatias)解釋說,正因為如此,那些說印尼語的人在印尼很容易被看著是"裝腔作勢、書呆子氣,或浮誇炫耀"。
事實證明,由於印尼語的過於簡單和呆板,這個為了統一印度尼西亞國家的語言實際人為製造了一個新的障礙,那就是阻止了國民之間更深層次的溝通。印度尼西亞人為了突破這個障礙,在生活中使用的是適合其特定地區、特定輩份和社會階級的極富個性的語言。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對標凖印尼語感到不滿的印尼國民有很多選擇。印度尼西亞有著數百種地區語言和方言,有時當地人只講當地語,有時則將當地語與標凖印尼語混合使用。我所在的日惹市位於爪哇島的中心地帶,也是歷史悠久的爪哇文化的傳統中心。在日惹,爪哇語十分常見,有些爪哇人使用爪哇語是為了表達對自身文化傳統的自豪感。一個食品供應商每天早上都在我所在的街道上推著他的木製小推車賣soto ayam(印尼語意為辣雞湯),和他談話時,他經常會混入爪哇語,讓我們的談話變得很難理解。最近有個問題他重覆問了我三次,我才聽懂。原來這是表達他為自己民族文化遺產而驕傲:我看過 wayang kulit(印尼語意為皮影戲)嗎?那也是經典的爪哇文化表演。
與此同時,隨著互聯網成為通俗的印尼語的新領地,印度尼西亞的年輕人繼續形成他們自己獨一無二的,更酷的語言變體,興高采烈地挑戰著老人家對語言的理解。印尼可以說是亞洲言論最自由的國家,年輕的印度尼西亞人是Twitter、Facebook、WhatsApp和Instagram的狂熱粉絲,他們在這些社交平台上用新詞和外來語(borrowed words)發展著自己的語言。當安迪妮和我在課堂上瀏覽印尼人的推特時,網絡俚語的頻繁出現使得我時不時就要停下來仔細理解詞義。
馬丁-安娜提阿斯告訴我,通過補充各種非正式和地區性的語言,年輕的印度尼西亞人在交談時"建立了親密和認同感",這樣他們才能更凖確地傳達情感,表達需求並講笑話。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然而標凖的印尼語仍然是我在這裏交流的最佳方式,而對我來說,這種語言達到了其最初的目的。當我使用標凖的印尼語時,我很欣慰地發現仍有不少人十分高興地與我交談。當某人以我容易理解的方式與我說話時,我能感受到對方的重視,知道他們很可能是為了我的方便,改變自己說話習慣,這是他們對我有意識的包容行為。
這是發生在我乘坐一輛摩托出租車從教室回家時的一件事。我能完全了解載我的年輕司機所說的每一句話。他的問題都使用簡單的短語:"在你的國家現在是什麼季節?"; "在你的國家有叫車軟件嗎?"。對我的問題,他也力圖以最清晰的方式回答。我尷尬地說了一個剛剛記住的俚語,他對我豎起了讚揚的大拇指。
要知道何時運用不同的語言風格,何時運用單一的語言風格,以及如何成功地平衡統一或多樣性的不同衝動——這就是官方印尼語以及印度尼西亞面臨的挑戰。
請訪問 BBC Travel 閲讀 英文原文。